
英文《习近平时代》主编、著名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熊玠。(资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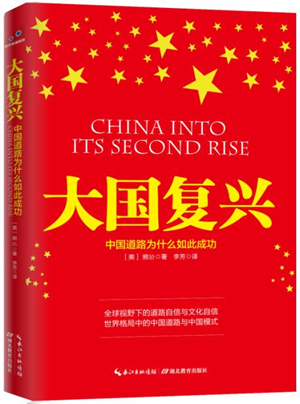
《大国复兴》中文版于2016年3月出版。
中国日报网北京4月18日电(记者 刘梦阳) 英文《习近平时代》主编、著名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熊玠的著作《大国复兴》中文版2016年3月出版以来,业界反响热烈。熊玠在书中详细阐释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为什么中国复兴不可怕?为什么质疑“中国威胁论”?中华文明的力量何在?著作对这些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却又很自然地引发新的思考——为什么以中华文明为探讨“中国复兴之路”的切入点?“借鉴传统文化而成的理想领导模式”在当今中国成熟了吗?“儒化”社会传统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哪些?为此,中国日报网书面专访了熊玠教授,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日报网:为什么想到以中华文明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复兴之路”?
熊玠:因感一般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通常均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而追其究竟,乃在他们均是由自己的(西方)文明与文化眼光来解释中国。这点貌似简单,但需要解释。
我所说的“文明”是概括了一个社会人群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人们所依赖生存的生计(农业、渔业、工业等),生命的内涵,大众公务之管理,彼此有无之互补与交换,文字与表达之工具,阅读与书写之方式,度量衡标准之统一,以及大众之人生观,甚至他们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与神明等等。而“文化”则是指一个社会人群的理想、哲学、一种共有的思索推理模式、包括较高的理智、艺术、道德上的表现。在某个意义上,广义的文明可说也包括了文化。而纵观文明又必须兼顾历史与其演进。
譬如,曾经名噪一时的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曾创立了一个据他说可以解释中国自古以来中央集权的理论。他说集权的来源在于中国人祖先耕种稻米需要有效控制与管理灌溉所需的水源。所以政府因参与提供水源的管理而介入了对人民生活的控制。这个理论走红一时。因为西方汉学家认为这个解释太科学、太合乎逻辑了。可是经过中国考古学家由挖掘出土的证据考证,发现中国人的老祖宗,最早是居住于西北部的黄土高原、那里没有稻米。他们完全靠种植杂粮度日。如此在黄土高原居住了几万年后才迁移到山下的黄河流域。那时,中国社会的文明与文化早已定型。以后从古印度介绍稻米进来,中国人才开始学会种植稻米。这个文明的实例,证明中国古老文明的形成远在中国人老祖宗开始种植稻米以前,因此完全推翻了魏特夫的理论。
因此,如要让西方人深入正确地了解中国,必须先让他们对中国文明(与文化)有一个融会贯通而纵观的认识。所以我写这本书,就是要以中华文明(包括文化与历史)为切入点。由于它同时也强调历史的纵观,因此本书可说是一气呵成;从而使洋人能从古到今对中国有一个踏实的整体观,从而更能正确认识当今的中国。
中国日报网:您在书中提到,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被称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这个提法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似乎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苏联模式”。您使用这个提法时是如何考虑的?
熊玠:要回答您这个问题,须分两方面进行:第一,须先指出这本书本来是用英文写的。在英文里面model的意思,不完全与中文翻译出来的“模式”意义相同。在英文版里我一再指出model是一个对实际情况的缩写(譬如书中第六章的6.3.1以及6.6节)。而且在第七章(7.1),我特意解释了model(模式)用在本书讨论中,是有以下诸元素的结合:即有其组成的结构(系统)、过程、憧憬(标杆目的)以及其他易见与不易见的元素。同时,我也指出,在中文“模式”有两重意义,即一个办事的指南,与一种让别人追随的“楷模”。我指出,所以在中国,论者均避免用“中国模式”,而习惯用“中国道路”。本书中文本的翻译,我虽然还没看见,但我相信一定也会照顾到我这里讲解的意义。
第二,在中国,自1950年以来,曾一度认苏联为老大哥,所以很多人一说起模式(楷模),即想到苏联模式(苏联作为中国的楷模)。记住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对别人而言,“模式”并不只是苏联所仅有。譬如,很多人揭橥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还有一个美籍日裔叫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学者,在苏联崩溃以后还夸夸其谈地创立了“历史决定论”,认为这证明,今后仅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唯一可模仿的model。可见“模式”并非苏联所垄断的。
中国日报网:您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比如儒家文化,哪些思想还可以适应当今时代社会,哪些思想已经过时?您提到“将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运用到处理国际关系中去,这在大量西方‘文化污染’的情况下是一种自然地选择”,您认为当今中国这种“借鉴传统文化而成的理想领导模式”成熟了吗?为什么?
熊玠:中国自汉朝以来,虽然经汉武帝在公元前136年将儒家思想定为国教,但儒教历经春秋战国到汉武帝时期,汉朝以后的儒家思想,其实已兼融有道、墨、法、阴阳等其他各家之精华,殆至唐宋以后,佛家思想的渗入,促成儒家“理学”之兴起。所以我们近代说的儒家文化,早已不是春秋时代的孔教,而是兼有儒、道、释各种思想精华融合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我们今日要恢复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绝非复古),就是要将中国文化历来百家的精华给予创造性的复苏,用以纠正目前物质文化泛滥成灾的恶果。
至于中国文化何以能克服国际上西方“文化污染”,道理很简单。首先,西方文化强调之“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变成两世纪以来西方欺凌弱小民族以及殖民霸权的借口。中国文化则相反地崇尚“和谐社会”之培养。并且在14世纪(明朝)至19世纪(晚清)五个世纪间那围绕中国的“朝贡制度”(或称东方的国际关系体系)已在中国的“厚往薄来”对待藩属(来朝贡之外国)的政策上得到身体力行的证实。今日美国身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在苏联崩溃后,更是独一无二的霸主。它的国防开销,一年达6000亿美元,比全世界所有国家国防开销加起来都多。但是美国却犯了“强不能安、富不知足”的痼疾。对此,我认为中国文化中强调的“内圣外王”可以作为借鉴,并起到振聋发聩之功效。兹解释如下:
“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之精髓。其中的“内圣”正是“救赎”,求诸内的意思,与西方救赎求诸外正好相反。“内圣”也者,即指内在精神修养,完善内心世界。这样的含义是指克服人间无安全感之道(救赎)不在求诸外。其结果是:内心世界完善以后,心灵不再空虚,没有必要再靠夺取外来物质财富(或强权)来填补心灵。相形之下,“外王”则是外在的功业建树,完善外部世界。按照孔子教导,在于个人而言,君子不独善其身,而须己立立人。在于一个国家而言,则须行王道而远避争夺霸权。美国以超强之地位,富甲天下之财力,犹不能安。譬如日日见中国之兴起而忧坐愁城。其故安在?一言以蔽之,只知争霸权,不知行王道,有以致之。争霸权,或许可以满足填补心灵之无安全感,但终不能服人。所以,既无“内圣”在先,则无“外王”于后。归根究底,美国要克服它“富不知足强不能安”的痼疾,最终须靠“内圣外王”之解药。这又必须先有昄依中国文化之先决条件。
中国今日提出“一带一路”政策,其构思与“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如出一途,即符合以中国文化中“兼相爱、交相利”之理想,达到“己欲达而达人” 的神圣目的。
所以,今日中国实现“借鉴传统文化而成的理想领导模式”,条件已成熟了。
中国日报网:根据您的分析,“儒化”使中国早早进入了“单一职业”社会,不仅是“学而优则仕”,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大于社会”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当今中国社会仍有延续吗?连年下降的公务员参试人数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儒化”社会传统有所动摇?
熊玠: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儒化”本身并非导致中国日后变成“单一职业社会”的后果,而是由于汉武帝在选定儒教为国教以后,并开始介绍初期的“科举”制度以开科取士。不但此也,在科举中的考试,儒家思想占领了特别分量。但真正让中国走向此“单一职业社会”的是科举制度(汉朝开始试行后,到唐代才将科举制度化与理性化)。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将儒教与科举影响分开。第二,中国自1905年以后科举制度已废除,国民党时代的“高考”制度(此与大陆今日考大学的高考不能混为一谈),以及新中国以来的干部甄选制度,绝不能和1905年以前的“科举”制度混为一谈。同时因为有现代商业经济与科技各行之兴,中国早已脱离了以往的“单一职业社会”。
第二,中国自身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起飞带动了职业多元化,所以做公务员的途径,与传统社会通过科举考试以求得“功名”晋身机会,已无法相比。难怪公务员参试人数年年下降。
中国日报网:您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并提出“历史上任何伪圣君的统治都最终堕落到为个人私欲服务,从无例外。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比缺少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来得更为实际”。您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这种“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有没有改观?为什么?
熊玠:其实,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缺乏民主意识。虽然论语中孔子弟子并没有记载孔夫子有关民主的言论,但夫子的“仁”与“王道”却奠定了“民本”的精神。所以孟子才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宏论。至于法治精神,我有另外一种看法。按照古书记载,孔子出生之时,“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兴、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孔子强调“忠”与“孝”,并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由此可观为何孔子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换句话说,他认为社会秩序,应以家法至上开始。因为如果由于家法严厉而管教成功,则社会上就不会有无法无天之乱臣贼子。就是因为如此,以后的祠堂法比国法更直接有约束力。但这个现象表明,社会秩序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家”与“族”的纪律、与个人之道德自约之上。
其实,“法治”的思想,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但自商鞅变法后,大秦实行的法治(制),实际是借苛刻无情之法纪以钳制人民自由与思想,其祸患无穷。再加法家之间彼此的勾心斗角,造成遍野怨声载道,使得大秦帝国之天下由始皇传到二世就被推翻。嗣后的中国人(包括精英分子),每听到“法治”难免就会想起秦朝“法制”贻害众生之先例。不过,有秦朝“法制”的声名狼藉,未尝不是一个堪可利用的反面教材。这个再加上一般人对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的记忆,等于是有助于建立“法治”之急需性的两个反面交材。换句话说,今日共产党要为中国建立新的“法治”观,除了可强调文革期间毫无法纪之不可再犯以外,还可对普罗大众解释,当今所要建立之“法治”绝非秦代“法制”之翻版。
中国日报网:您否定“中国威胁论”,并不认同“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等观点,目前西方学界、社会对您观点的认可度如何?
熊玠:我不同意“中国威胁论 ”,在我书中已经指明自从17世纪有国际社会以来,凡是第一次崛起的国家,均是要称霸而造成对别国的威胁。但是,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崛起。中国人自己也许没有数据,但外国人有。我参考了英国的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及其他外国人的数据,证实中国在公元元年起到鸦片战争(1840年)的前夕,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GDP,比全部欧洲加起来都要多。不但此也,中国在第一次崛起的将近2000年中,也没有侵略他国的记录。所以我对“中国威胁论”持相反意见,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过去20年中,西方学者已出现四种不同对“中国威胁论”质疑的意见。我称之为三代异议的轮番。第一代,是针对主流“新实权派”曾经预告中国崛起将难免有要均衡美国霸权的风险。可是,事实已证明中国兴起(再起),并没有企图要均衡美国的霸权。有人还指出到目前为止,只看到美国在企图均衡中国,而非是中国均衡美国。第二代的异议则是说中国仅有了国力,并不一定就要争夺霸权,还需要看它有没有争霸权的动机。第三代异议是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的兴起。因为虽然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但在中国的投资几乎全是来自境外或与外界有挂钩关系,所以在这种深度错综复杂依赖的关系里,如果中国要反目成仇,岂不造成自戕的后果?
中国境内经济取得成功,并带动了全球经济在2008年以后的复苏。这样的发展,已经开始促使很多西方(包括美国)有名学者改变或者修正了他们当初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评价。譬如,最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模式》的书,作者是在美国曾名噪一时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教授,现任教于清华大学。他将中国的政体称之为Meritocracy (贤能政权),并认为这个制度比民主制度要高明。据我所知,此书与其揭橥之意见在美国学界(包括哈佛大学)引起相当共鸣。
中国日报网:去年,您的《习近平时代》英文版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中文版也即将于今年在国内问世。您写这部书的动因是什么?您认为 “习近平时代”最特别和突出的地方是什么?
熊玠:首先,我须指出,《习近平时代》这本书,我是主编,实际写作另有四人,而中文译成英文的另有一人。我之所以担承主编的工作,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想,引起我极大的共鸣。由于我撰写《大国复兴》(英文版于2012年问世),曾对中国复兴再起的问题上花过很多心思,因此对习主席揭橥复兴之号召,尤其是他的复兴要经过两个阶段(2021年和2049年)的主张以及要重整中国故有文化各节,特别“于我心有戚戚焉”。当然,除此之外,“习近平时代”最突出与特别的地方,还有他的“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以此来领导全民奋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另外他还策划大国关系之新规范,冀创国际新秩序之格局。总之,我是在有一股“精神感召”的大气氛之下担任该书主编的。
(编辑:吴彦鹏 王辉 周凤梅)
